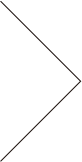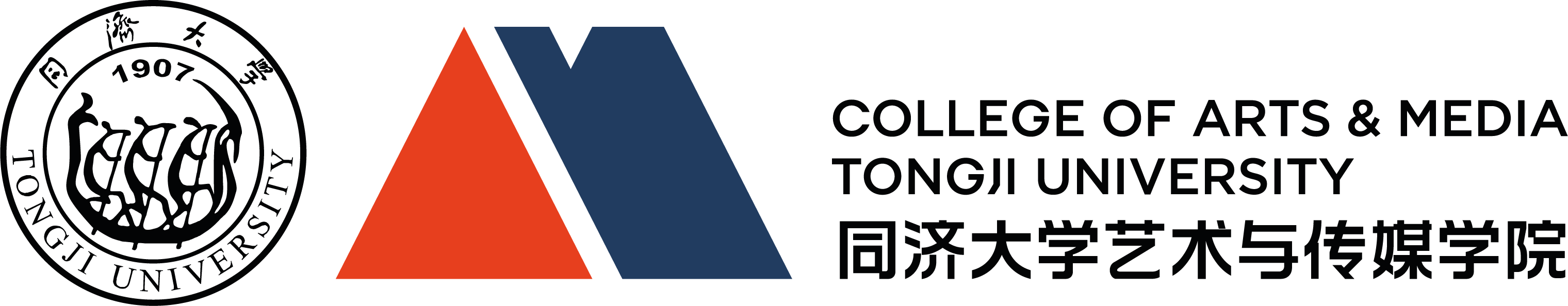本期惟新前沿将带来我院蒋原伦教授的文章:《庄子心目中的孔子》。
原文发表于 《文史知识》 2023年第二期。
写下这个题目,不仅是表达一种见解,也是对自己以往认识的一种纠正。因为在我印象中,庄子是一直喜欢怼孔子的,或尖刺或挑逗或戏弄,总之没怎么待见这位圣人。这里有读庄子的某些文本(如《盗跖》《渔父》)的原因,更有少年时,整个社会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当然庄子的洒脱和笑傲江湖与孔夫子的谨言慎行也是一种对照,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
钱穆先生在其《庄子纂笺》的开篇就说,《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这话自有其道理,但是细想,历朝历代均不乏治庄者,很难用盛世或衰世来区分,倒是能用个人的穷通和困达来解释,即与其用时代这个大背景来参照,不如下沉到具体个人的际遇更有说服力。
在中国的思想源头上,有先秦诸子百家,那时呈现一片辉煌景象,说星汉灿烂可以,说鱼龙混杂亦可。可惜流传下来的文献却大不如人意。如荀子在其著述《非十二子》中所批驳的那些子们,除了墨子和孟子等几位,其他诸子的书今天已经湮没无闻。所谓书有“十厄”,从秦始皇焚书算起,经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再到靖康之变,许多珍贵的学术典籍都灰飞烟灭,只有儒家和道家等一些文化典籍的保存相对完整,所以后来的文化人在治学上也没有太多的挑选余地,不管你是否服膺老庄之学,老子庄子的书就摆在那里,再说,即便是规规矩矩的儒生,心目中也有一个逍遥豁达的庄子在。当然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儒家和道家的学说有其社会需要,所以不管社会如何动荡,兵荒马乱,其香火照样能赓续不误。
儒家和道家,一入世,一出世,构成了文化功能上的互补。不过这“互补”,往往是以道家补儒家,而非儒家补道家,由于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受现世的种种俗务和烦恼困扰,因此能给予人们解脱的往往是道家文化或者佛教文化。其实儒家文化的内涵中也有解脱之道,修身齐家之后不一定非要治国平天下。许多读书人习焉不察,在这篇文章中暂时不表。
一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庄子心目中的孔子,其时孔子的形象尚未定于一尊,是有点儿驳杂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于庄子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为在《庄子》这本书中,提及孔子的地方非常之多,且在篇幅和字数上也超过了老子。 一般认为,庄子一书三十三篇,不全是庄子所作,其中的内篇为庄子真传,这一点在学界基本没有异议。以内篇七篇为例,庄子提及了许多上古人物和先贤如:尧、舜、许由、商汤,伯夷、叔齐、老聃、孔子……这些人物在庄子笔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个个都逍遥,实际上这也是庄子的逍遥游,游走于历史长河之中,笑谈于先贤群英之间。但是在其中,孔子占的篇幅最多。光在内篇七篇中,涉及孔子的就有四篇,一些篇章如《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等,都大段“引用”孔子和他学生的对话,展现了夫子对弟子和后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风范。这些似都表明在庄子时代,孔子思想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其时孔子过世百多年,尚没有什么官方加封的吓人头衔,而那时的所谓官方,周天子自身也摇摇欲坠,即便加封也无人理会。至于那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由此可以判定,孔子的思想学说在民间士人群体那里已有广泛影响,成为谈资,成为不可忽略,难以绕过的思想高地。前文之所以在“引用”上打引号,是因为许多孔子的言论并非孔子所说,乃庄子所杜撰。庄子的文体有“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之说,说的是他的表述中有大量的寓言和名人名言,那些寓言灵动而诙谐,是庄子“齐物”或“鱼之乐”智慧的结晶,而那些名人名言(即重言)是庄子假借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之口,说出的是他自己深邃的思考和惊世骇俗的见解,这也可以看成是庄子说理的一种修辞方式。或可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在庄子那里已经有了端倪。
不管人们有没有细读庄子,这位先哲留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逍遥自得,这倒不全是《逍遥游》据全书的首篇,或各种教材选本中赫然在目的缘故,而是千百年来,逍遥似乎就是庄子的别名,我甚至错觉,在辞源上该先有庄子才有逍遥之谓。台湾学者傅佩荣的庄子研究著作的书名就是《逍遥之乐》。不过读了《人间世》、《德充符》等篇章后,会诧异,这难道是写逍遥游的同一个庄子?逍遥游气势磅礴,居高临下,远离人间烟火,而《人间世》则一上来就是孔子和颜回的对答,讨论的是一些十分世俗而功利的话题,即如何侍奉或应对人君。颜回欲去卫国,辅佐国君,征求老师的意见。在师徒间周详而设身处地的对话中,读者可以见出孔子洞察人事的绵密思虑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实际上是孔子在教导颜回如何处理复杂而不确定的君臣关系。接下来 ,叶公子高将出使齐国,求教于孔子,又是一段类似的对话,既有天地之命又有君臣之义等等。一个老到的,富有政治智慧的孔子形象跃然于笔下。前文已经说过,学界没有人怀疑内篇是庄子本人所撰写,我想的是《逍遥游》和《人间世》,一在九万里之上鸟瞰,一在人间世忙碌,分别是庄子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所撰写?虽然《逍遥游》的篇目在《庄子》全书之首,但是在写作上可能晚于《人间世》,因为前者的境界和豁达不是天生的,是在人世间历练后的彻底醒悟。但是反过来说也通,即《逍遥游》是写于早年,那时庄子年轻,想象力丰富,气盛而言殊,到了晚年,既受孔子影响,现实生活经验又侵蚀了奇瑰的想象力,所以只在人间世打滚。
接下来的《德充符》应该是与《人间世》同一个年代所撰,虽然在《德充符》一文中,展现了孔子的另一种风范,但是这正是儒家仁义的风范。在此文中一连出现了几位兀者和面目丑陋的人,所谓兀者即断一足之人,这些形体上有缺陷或者不完美之人,却有着常人所不能企及的德行,第一位是鲁国的王駘,据说“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 即王駘门下的学生与孔子一样多,似乎整个鲁国的有志青年,一半跟了孔子,另一半拜倒在他的门下。王駘的授徒的方式也有些特殊,“立不教,坐不议”,但是每个学生都能“虚而往,实而归”,也就是说王駘能以超于言语之外的教学方式让每个学生都有充实的收获。这情形是有点蹊跷的,像佛祖拈花迦叶微笑那般神奇,其时佛教并未传入中华,不过从后来儒释道三家合一可以看出,当初应该是有那么一些端倪的。孔子的学生将此情形告诉孔子时,孔子的反应是“夫子,圣人也……丘将以为师”。因为王駘做到了“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这几句话按一些学者的解释,他能处于无所凭借的境地而不受外物变迁之影响,主宰事物的变化而执守事物的枢纽。
除了王駘,还有几位兀者,如申屠嘉、叔山无趾等在德行方面,各有出色的表现。他们都是内心光明磊落而处事淡定,大度,从容,不卑不亢之人,均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和称颂。这里,我们可以追问的是庄子为何将德行和身体残缺的人联系起来?另外,又为什么要假借孔子之口,说出这些道理?在庄子那里,内心的修为和外在的形体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事情,庄子之所以在通篇之中拈出的都是形体残缺和面目丑陋之人,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显然,在庄子的价值观中,内心生活的重要性优于外在的形体之美。立身之根本,不在于外在形体,而在于内在的修行(偶尔我会联想到庄子本人的相貌如何?有没有引起过他人非议)。其实,哲学思考的第一个飞跃,就是将有形的世界与无形的道(或者说逻各斯)分离开来,或者说从世界的表象中探究事物的内在本质,并从感性中升华出某些人们称之为理性的东西。人们情感上倾向或喜欢貌美之人,但是外形的美丽并不一定可靠,所以庄子干脆矫枉过正,虚构了三四个兀者和貌丑之人,并让他们分别于对话于孔子,老子,郑国的大夫子产和鲁国的国君等,以表明他们的高尚,这高尚是境界上的高尚,而非社会地位和身份上的高贵。庄子通过孔子说出这些道理,是为了赋予这些说法以权威性。在道家那里,内在的道和外在的形不在一个层面上,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所谓“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等等都是,但是一般人未见得这么认为,所以要借助孔子之口借以推广,由此也可以推断,其时孔子在士这个阶层和年轻的学子那里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非同小可。而且孔子在《德充符》中显得特别谦逊和低调,善于检讨自身,不以有德者自居。
自然,庄子写作《德充符》并非为了塑造孔子形象,他只是觉得这一番大道理必须由孔子来说出,才够分量。由此,读者领略到的孔子是一位谨慎谦虚,胸怀宽广,善于学习他人长处之人。这一形象也延续到了《大宗师》中。
《大宗师》的篇名是有点惊悚的,以为是武林高手或者黑道老大要出场,结果并无这类人物。大宗师既可以看作是某位世外高人,似乎也可以看作一种行为。如在陈鼓应看来,所谓大宗师,就是“宗大道为师”,或者师法大道的意思。这回孔子出场,面对的是一群不拘社会礼俗的人,朋友死了,他们却对着尸体弹曲唱歌;母亲仙逝,脸上有哭泣,心中无悲戚,所谓“居丧不哀”。孔子的学生不解,就跑来问老师,孔子则称那是一群方外之人,不能以一般常人的礼俗来要求他们,于是又讲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的一番道理来(即在某些得道之人那里没有生与死的严格区分,故他们能坦然面对生死,顺其自然)。此篇中最有趣的是当颜回说出自己进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境界时,孔子表示要追随颜回之后。所以这篇里的大宗师,也许就是颜回了。
读者会发现,在内篇中所有复杂一点的道理都让孔子来开口,孔子似乎是说理者的化身,他能对许多不同的事物和现象作出精辟的阐释,并能窥见最高最根本的大道理。按理在文本中,孔子就是庄子的代言人,不过有时孔子又像是作者的一位对话人,文章思路的推进有时需要借助这么一位对话者。这情形有点像柏拉图的对话录,在对话中,思想的火花迸发激荡,真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二
许多研究者认为外篇和杂篇可能是庄子的门生和后学陆续撰写,之所以如此判定,有各方面的理由:有的是从文风来推测,有的是从文章中所提及的事件来判定,也有的从思想内容着眼,认为外篇和杂篇中的一些说法和内篇相抵牾和扞格。其实从这些文章所“引述”孔子的言论和对话中,也能见出分野。在内篇中,孔子基本是一位圆满的智者,德者,对各种事务应对自如,进退之分寸把握恰如其分。在外篇中,情形就不太一样,孔子的形象明显褪色,地位也下降。对世事显得不怎么有把握。特别是他与老子相见时,自信心也略显不足,基本上是只有聆听后者的教诲和指点的份儿。老子问他学道如何,孔子称学了十二年,仍未得道。这情形有点悲催,当然,从活到老学到老这个角度讲,人人都在路上,这也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在杂篇中,情况更为不妙,孔子成为揶揄和挖苦的对象,不仅书生气十足,而且还有点伪善,与内篇七篇中的孔子形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故苏轼铁定认为《盗跖》《渔父》等篇为伪作。
这里先说说外篇。外篇中有《天地》《天道》和《天运》,均为高屋建瓴之作,起调就上了概念的天花板,由天地之广大,天道之运行说起,有后来者居上的气派。所以说外篇是庄子门生或后学所著,不无道理,抽象的道理是要前赴后继,步步推进的,庄子虽然很厉害,但是弟子们毕竟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且其中应该有青出于蓝者。
在《天地》篇中,孔子弟子子贡见到一丈人抱瓮取水灌溉菜圃,颇劳累,于是好意提议用机械灌溉,可“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不料却反被丈人批评子贡是以机巧之心取代淳朴的心性,同时批评了孔门弟子,认为他们是一伙以博学自夸而获取声名的人。这算是比较严重的批评了,怎么由子贡的善意建议一下子就跳跃到对孔门全体的批判呢?不过如果看作是道家对于儒家的观念批评,而不是一个菜农对于子贡的指责,这就比较好理解。
那么孔子或儒家是以什么博得名声的呢?是以机巧之心吗?好像也不是,其实儒家的声名就在于周游列国,提倡仁义。在这方面孟子算是一个典型,他四处游说,劝说君王施行仁政,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徒有虚名,这大概给庄子及其门生留下了把柄。也因此在《天道》篇中,老子与孔子的对话,直接批判了仁义。孔子认为“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而老子则认为,兼爱有点迂腐,无私实际就是偏私。进一步,老子说道,“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 一切均自然运行,在此之上硬要再去揭示什么仁义,那就是乱人之性情。
同样的意思,在《天运》篇中,大致重复了一遍,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结果又被老聃一通批驳:“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 膚,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愦吾心,乱莫大焉。” 意思是糠麸眯眼,蚊虫扰睡,仁义乱心,而且是最大的祸乱。批评的焦点还是落在“仁义”两字上,这是道家对儒家总体性批评,此情形在内篇中是未曾有过的。这不仅表明道家的基本思想不同于儒家,而且也明确了儒家的核心观念,可以概括为仁义。这仁义虽然是儒家独产,但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追溯起来,儒家的话语往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过来,于是文章又从三皇五帝说起,描述了一条治国的路径,黄帝如何,尧如何,舜如何,大禹又如何等等,尽管观念上层层推进,治理上层层加码,但是在道家看来,总体上是越治理越差,可谓每况越下。原本道家提倡无为而治,所以从上古一直数落下来,也是符合道家学说的逻辑。今人一提起无政府主义者,往往会联想到法国的或俄国的谁谁谁,其实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是中国的道家。
按理,在道家的词典里是没有与时俱进概念的,因为在道家看来,那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是最为和谐的时代,所以远古时期最好,当人们从外部干预社会,强加各种理念于社会管理之上,哪怕是天皇老子,哪怕是圣人再世也行不通。所以“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 这越治越乱的原因是人类的智慧往往违背天理,即“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暌违)山川之精,中坠四时之施,其知僭于蠣蠆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亦可耻乎,其无耻也?”(“蠣蠆”和“鲜规”是指毒虫和小动物)正因为三皇之知不仅违背天地日月的运行,而且还有毒性,而他们偏偏还要以圣人自居,这就显得十分可耻了。难怪道家的思路是弃圣绝智,反对机巧之心,甚至要回到三皇五帝之前的蒙昧时期。
但是不讲与时俱进,不等于没有顺势而为,道家认为孔子和儒家倡导周礼,是不合时宜的做法,礼义法度者,是应时而变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还要返回到以前,去行周公之礼,就像让猿猴着周公的衣服那样可笑。这里说道家顺势而为,不够准确,道家的意思其实是顺势而不为,“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见《应帝王》)因为人为的一切都是破坏自然状态的,所以儒家的有所作为不仅是徒劳,而且是违背天理的。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自然呢?在道家那里“自然”似乎是一个终极概念,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只是在老庄哲学中,我们无法追问什么是自然,自然是最原初的存在,也是逻辑的尽头,无论是“自然”而然也罢,顺其“自然”也罢,都暗含着一种原始的或永久的秩序,但是谁也无法溯时间而上,到达那个自然的源头,所以自然因其不可捉摸而有着统摄一切的神秘性,这一神秘性又由“道”来概括,神秘加莫测。如此一来,儒学中的任何说法和概念都无法与其匹敌。因为儒学中的概念,都是比较具体的,可以践行的,比如“仁义”中的仁,大抵是“仁者爱人”,或者“克己复礼为仁”云云,因为仁或义,无论怎么界定,都是人的一种行为(至多包括相应的思想观念),既然是人的行动,就有可能会出错,所谓动辄得咎。而庄子这边的一些概念,不管是承老子而来还是自创,高蹈虚空为多,因此打起口炮来,道家比儒家要灵敏得多。
当然,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也不完全是口舌之争,而是通过对仁义的批驳,道家宣扬自身的理念和价值观,因此在外篇中,老聃出场的机会就比在内篇中多得多,发表的见解也更加完整而系统。
三
前文已经提及,学界一般认为除了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其他诸篇可能是庄周的门生和后学所完成的。如果以内篇为标准,从文章的文风,体例,思想内容综合来看,外篇和杂篇确实不像是庄子本人所著。《庄子》一书究竟成于何时已不可考,不过,据史记记载,庄周“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即表明起码在汉代之前,《庄子》一书已经成形。庄周的学说在当时虽然有影响力,只是没有像其他几位子学大师那般领时代之风气,有一大帮弟子紧随其后帮衬。到了魏晋,世风陡转,玄学兴起,庄子大显,于是出现了多种注本,有司马彪的注本(五十二篇),有崔譔的注本(二十七篇),有向秀的注本(二十六篇),最后才有了郭象的定本(参见方勇《庄子学史》第一册)。说郭象的庄子注为定本,并非其他的注本就此消失,起码在唐代还有学者能见到司马彪等的注本,但是后世的学者认为郭象的注本最为靠谱,所以在流传过程中,别的注本就逐渐湮没,只留下些许蛛丝马迹。
从司马迁“十余万言”,到定本的不到七万字,从司马彪的五十二篇到三十三篇,郭象剔除其中的“妄竄奇说”,是下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的,不过这内篇,外篇和杂篇分野的保留,还是露出了端倪。
唐人成玄英在给《庄子》一书作疏时认为:“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眀于理事。”这种说法其实是有些勉强的,因为在《庄子》的各篇中,虽有说理和说事的多寡之分,但是基本上每一篇都是既说事又说理的,所以成玄英接着不得不补充道:“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
笔者认为,这内篇,外篇和杂篇的区分,能见出道家在其流播和发展过程中对儒学整体态度的阶段性变化,亦可说孔子的形象在庄门那里是渐变的。即在庄子自身的年代,儒学气象颇宏阔,趋从者众。所以,庄子借重孔子要多于老子,并没有把其作为对立面来批判。随着战国后期纷争形势的加剧,儒学宣扬仁义四处碰壁,撞南墙而不知回头,这就给批评儒学的人留下了靶子。庄子的后学们于是在外篇中推崇老子的无为,批评仁义的不合时宜,由此老子不断现身,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孔子指点迷津。
到了庄子的杂篇,情形又有不同,大概儒道之争越发激烈,所以在《盗跖》《渔父》《列御寇》诸篇中,道家直指孔子的伪善。如盗跖面斥孔子:“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又说,“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在《列御寇》中,则通过鲁哀公和颜阖的对话中,把孔子描绘成巧言令色,讲空话大话,不能干实事的巧伪之人,至于《渔父》篇,基本是从头挖苦到尾。
总之,猛烈而尖刻的、某种意义上带有人身攻击的文章均集中在庄子的杂篇,不能不令人起疑,所以尽管郭象下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后人还是觉得,这杂篇中的许多篇章是有问题的。如宋人苏东坡认为,杂篇中的《盗跖》《渔父》《让王》《说剑》显然不是庄子所作,因为内容倾向上跟内篇完全不同,内篇是助孔的,而《盗跖》《渔父》则是诋孔的。至于《让王》和《说剑》则“浅陋不入于道”,也不像是庄子作品。还有一些篇什是将别处的作品,如列子中的作品混入《庄子》的,这样一来,苏轼几乎否定了一半以上的杂篇。
其实,郭象不至于不清楚杂篇的内容和内篇相抵触,或者《庄子》中各篇非出自一人手笔。任何人只要读过庄子末尾的《天下》篇,就清楚此篇非庄周所著,而是庄子的后学对此前那个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的概括性梳理,郭象怎能不知晓。郭象在编撰庄子一书时,可能只是将内容重复的,或者过份粗糙的文字删去,他一心想弘扬庄子的学说,并非是想将庄子和非庄子作出区分。毕竟几百年过去,先秦的“古文”几经转抄,成为汉代以后的“今文”,没有人具备某种特殊技能和相应的自信,可以将庄周本人和他的弟子的文本严格区分开来,郭象亦然。只要认可庄子一书中的一些篇什为后学所著,那么就无所谓“伪作”,只能说先贤和后学的时代背景不一样,观念就有了变化。
不过,由内篇的所谓“助孔”到外篇的批评儒学的仁义观念不合时宜,再到直刺孔子,这里应该有个时间跨度,在这段时间里儒道之间应该是有过许多思想交锋的,当大量的历史文献消失,历史语境无法还原,后人读《庄子》全文,会有许多困惑和不解。即当我们将不同时期的文献作为同一时代的作品来读解,将历史过程扁平化,就会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从外篇的温和的批评,到杂篇的严厉尖刺和无端攻击,只在一念之间,或者认为庄子的文章前后矛盾,必有蹊跷,必有伪作,再或者演绎出庄子学中孔子的的几副面孔等等。其实,我们如果想像《庄子》一书是在庄周本人去世后,几十年间由其门生和后学逐渐添加,汇编而成,而后学在与儒家的辩驳中,互相抬高嗓门,于是就有了外篇。继而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又有了杂篇,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四
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其实真正称得上百家争鸣的好时候也没有多少年头。春秋时期诸侯众多,每个国家的国力相对弱小,养士都有困难,所以到战国中后期才有实力网罗人才,有了人才的聚拢,才有思想和学术的交锋和争鸣。稷下学宫的出现像是一个神话,据说“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学士复盛。”(《史记 田齐世家》)所谓争鸣,各自著书立说,发表见解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情况是面对面的交流、讨论和争辩,那时候书写工具十分古老,书于竹帛十分麻烦,所以大量的议论和争论不可能都著录于文字,由此我们不妨猜想,孔孟的徒子徒孙和庄子的门生频繁过招,后人看到的文献只是那时争论情状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例如儒门的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必然会受到庄门的反击,后生可畏,他们直接对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鸣鼓而攻之,也许就抛出了《盗跖》《渔父》《列御寇》等篇什,顾不得自己的师父曾经如此敬重过孔子。
笔者如此揣测,是因为庄子一书的末篇《天下篇》,该篇乃是庄子的后学所为,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学说评点是颇中肯的,故章太炎先生论诸子流别,首推此篇。我们也可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微型学术史概论,它评述了十二三位在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前辈,即便有所批评,也口气雅驯。与此相反的是荀子的《非十二子》,一口气喷了十二位大人物,其中提及的墨翟、宋鈃,田骈,慎到,惠施等和《庄子 天下篇》是重合的,不过荀子的批评显然要比《天下篇》严厉得多,因为他只有“非”而没有“是”,笔锋所向,横扫天下。可想而知,一定会激起各种反对的声浪。荀子倒是没有门户之见,他连子思和孟子都批评,所以道家和墨家等更不在话下。不过由此一定会招来各家对儒学的反批评,有些就可能汇入了庄子的杂篇。要说也是,当初庄子一门对儒家的先辈是充满敬意的,称“於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谓褒扬有嘉,连二千年之后的章太炎也看不下去,认为《天下》篇在此处“不加批判”,有点说不过去。即由此推想,不一定是庄子后学率先攻击和诋排儒学,他们可能是为了反击儒门对道家学说或其他学说的严厉批评,才创造了渔父和盗跖等彪悍的人物形象。
其时,人们对儒家善意的批评,就是指他们不合时宜,身在战国而奉行周礼,身在乱世而推行仁政。对儒家的人身攻击,那就是“伪巧”。庄子的外篇和杂篇是在一种相对自由的氛围中,以上两种情绪和批评的综合反映,所以《庄子》实在不能看成是类似《孟子》《荀子》一类的个人著述,它是一部反映战国中后期,庄子及其门生对儒学前后态度变化的文献。在其中,读者既能体悟到庄子对孔子的敬仰和精神寄托,也能窥见庄门后学对儒学的批判和嘲弄,当然更能领略到二千年前百家争鸣的弘大气象。